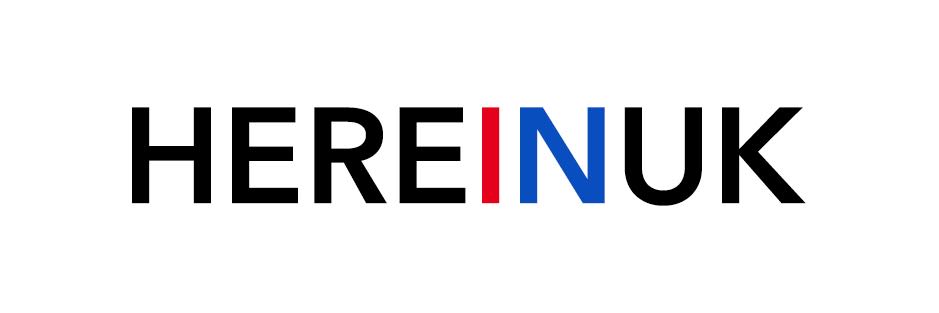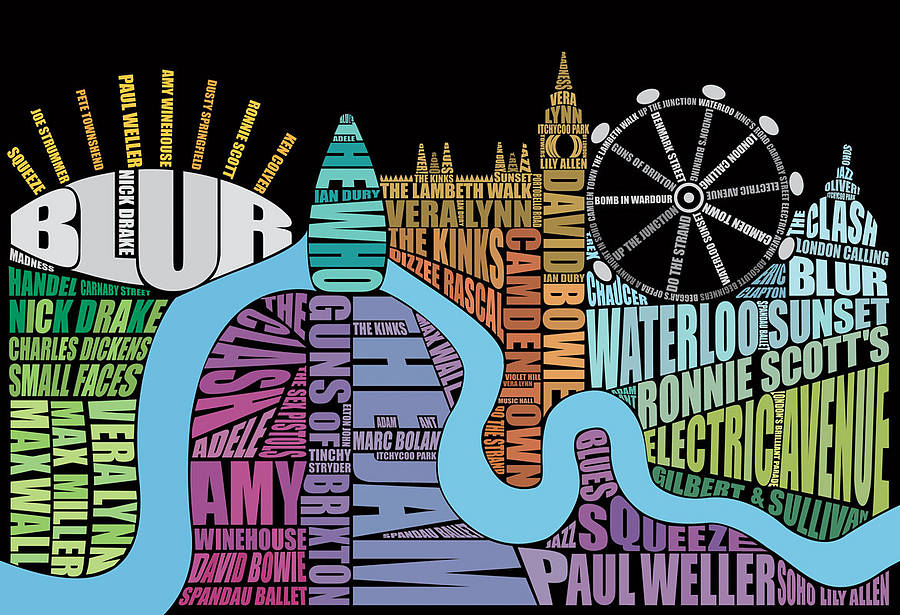“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布里斯托靠海,也很 “山”,我没有发现过蓝精灵,却常发觉这山城里充满了背着包爬坡的人,大包、小包、书包、公文包被裹挟在生活里,流淌在布里斯托交错的,高低起伏的路上,经过一幢幢时而维多利亚式、时而乔治式的屋楼,在转角遇见或完整而庄严、或残旧又疲惫的石房子,最后消失在各自的防火门后,形成山城的节奏。这些临街的门,常常因为街的陡,形成一个个和路面的夹角。而能让这 “不得已才出现” 的无奈的夹角变得颇具气势和自豪的,只有地标帕克大坡(Park St.), 山城最“山”的坡。山城的各种片段,全散落在大坡的两头了。

站在北面的坡顶往南看,眼角余光扫到的是坡两边嵌有格子窗的蜜色乔治时期的建筑,沿街都挂着大幅招牌,大多是主流服装店和食店。坡上不时有上坡累的岔了气,或是下坡溜得太快刹不住车的路人顺势冲进店里的平地,调整步伐后再上路。从前戴着礼帽的,做布匹、酒、或是奴隶贸易的绅士,以及他们家拎着许多食物疾走的仆人,在这种狼狈的时刻,也是这样歇脚的吗?不知那位就住在大坡边小路上的叫约翰平尼(John Pinney)的商人,每次从他淡绿色调的家走到坡上时,有没有常常抱怨?也许更多时候,这抱怨早被奔到坡下码头边迎接自己货箱的满心欢喜冲淡了吧,他的方糖和烟草生意带来的丰厚利润足以让他笑口常开。

坡底东侧的一面墙上,一个裸男单手吊挂在窗檐外,试图躲避窗口正在四处巡视的情人的丈夫。那是著名涂鸦艺术家班克西的作品,而更多让山城闻名的涂鸦,则出现在通往东边市区购物中心的路边,光怪陆离的作品吸引着游客和滑板少年,让那里充满了街区亚文化的玩世不恭的气味。被取代的,是这片区域作为中世纪旧城中心的古典和秩序。涂鸦墙对面的西边是一大块草坪,被夹在乔治式新月形市政厅和十一世纪的大教堂当中。天气好的时候草地上会有不少闲坐的大学生,以及特意在市政厅对面支起帐篷驻扎抗议的人,让人不由得把晒暖的愉悦的心稍稍收紧一些。阳光下,山城的现在洒落在过去上,彼此平静地相处,却难掩微微的冲突感。

坡底的喷泉小广场边是古老的护城河Avon River,河水穿过城市,静静流向卡迪夫湾。沿河而西,Arnolfini现代艺术馆立在中世纪的鹅卵石小道上,路边排着浓荫高树。夜晚,沿河的酒吧和餐馆把灯珠悬浮在暮色和水影里,河边停靠的没有帆的小船也随之褪去白天的颜色。河湾处的Mshed城市博物馆门口,有旧时蒸汽火车开过的铁轨,工业革命时兴盛港口的吊机还不知疲倦地把手臂高高举向天空,好像害怕被遗忘一样。就在那吊臂下,一位老奶奶曾向我抱怨,整修过的博物馆拿走了以前陈列的打印机,让她很不开心。沿河再往前,制造于两百多年前的大不列颠号如今在这里最终停靠,它是第一艘横跨大西洋的用螺旋桨驱动的汽船。它的著名设计者布鲁内尔在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再次成了大明星,而他的另一件作品,布里斯托吊桥,则隐在城市边缘大块的绿林中,从帕克大坡上就能望见。那个绿林在每年夏天举办的世界热气球节上为人们放飞了许多表演和愿望,也让我在一个微醺的午后拾得了一个油绿喷香的松果。

如果爬上坡顶的高塔,俯瞰下去,看到阡陌交通和各色屋顶,大概就能感到这城市的新的、旧的时光切片,像书签一样隔在了城市的书页里。最早的一片,是撒克逊人的村庄兴盛在Avon河畔,最新的一片,是人们在相似的道路上,和从前的人一样,慢慢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