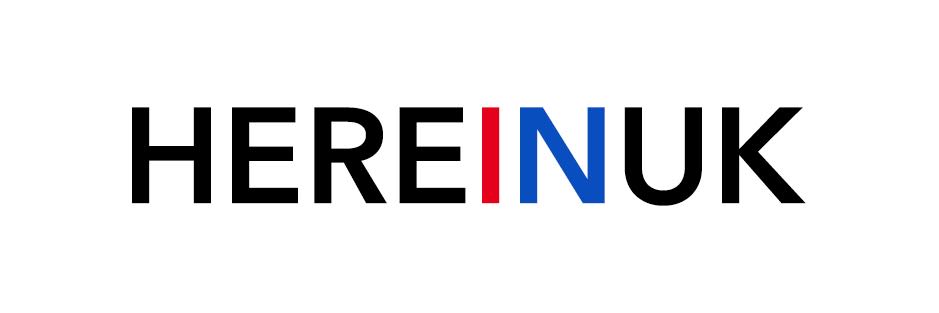记忆里最好吃的甜点,是小时候爸爸从好利来买回来的“鲜奶蛋糕”。在那个日新月异的时代,
当“鲜奶蛋糕”横空出世,统治蛋糕界多年的那些油腻甜硬的“奶油蛋糕”就群体毁灭了。
“鲜奶蛋糕”被我视为神物,每当我郑重地掀开好利来清淡的蛋糕盒子,用小勺挖上一块放进嘴里时,
整个人像是扑通一下坐进云朵里,心刹那间就消融了。
爸妈都不喜甜食。他们对甜食的一贯冷漠总是让我心生失望,时而硬逼着他们尝上一口,
他们所能给出的最高评价,也只限于“不太甜,还可以”。
来到英国后,我终于尝试到所谓“甜”是个什么概念,也终于体会到不喜“甜”的人的心情。
甜到发酸,甜到发苦,一颗巧克力放进嘴里,没有咬下去的勇气。当糖浆划过喉咙,被烈性甜呛出眼泪时,
我几乎对大英帝国的所有甜食丧失了信心。
又是嘴馋时,逛进超市去,看着太妃糖,糖衣蛋糕,草莓冰淇淋,薄荷巧克力,苏格兰黄油饼干等等等等
这些历史悠久的经典零食逐个从我眼前飘过,一圈一圈地转啊转,徒增空虚。
第一次去梅森˙比尔陶克斯 (Maison Bertaux)甜品店那天,我正一个人在伦敦西区闲逛。
游走在错综复杂的小巷道中,没方向,穿梭于鳞次栉比的小店铺,又乐此不疲地购买一些没用的东西。
华灯初上,大雨不期而至,西区沉静的大剧院,纷纷拉开古老的幕布。
撑起伞,蹲在街边翻看一本厚重的伦敦自助游手册,侧着脖子用力夹住雨伞,伞还是滚到地上去了。按图索骥,当我隔着雨雾,终于找到了这家被伦敦老饕们盛推的“拥有神奇力量的”甜品店时,
路边的雨水被我踩得噼啪作响,我高兴地摇头晃脑。
甜品店外,露天的小方桌,蓝白相错,置身于大雨之中的花瓶,宝蓝色的枝叶猛烈摇晃着。
隔着玻璃窗,看见草莓塔,葡萄干司康,可颂面包,布朗尼,鲜奶条,黑森林……
在月亮灯的照耀下拥挤着,熠熠闪烁。奶酪蛋糕看似格外走俏,刚卖空,又摆上了一个新的。
小店成立于1871年,是伦敦最老的法式甜品店。
听说老板来自奥地利,老板娘是法国息影女星。店面很小,分上下两层,推门进去时,楼下已座无虚席。抬头看见房顶悬着粉色的薄纱,吧台右边挂着深黑色大公鸡。人过多,柜台后的老爷爷略显不耐烦。
他身后的摆饰杂乱堆砌,装饰品让人匪夷所思。
我望着众多甜点不知如何是好,问了哪些甜点不甜。
老爷爷推荐了水果馅饼,但我还是指着旅游册子,点了所谓最有名的“白朗峰”。
踏着窄小的楼梯走到二楼,鹅黄色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幅怪诞抽象的插画,
歪着脖子看了好长时间,想起了冯小刚《大碗》里葛优做的葬礼策划案。
二楼房顶上悬挂着五彩的塑料拉花,镶嵌在墙壁上的长沙发上,聚着一群中国姑娘。
我在墙角坐下,瞟见墙壁上涂鸦风格的小画。
服务生很快端来了“白朗峰”和一壶红茶。
“白朗峰”全身白白的,顶上一层厚厚的奶油,清爽奶香浓,中间是一层颜色略深的奶油,起初以为是巧克力味的,但吃起来与第一层并无不同,最下面是用蛋白烤制的底儿,硬脆的,用小钢勺切下去听见嘎吱一声,
吃进嘴里,眉头马上皱起来,还是太甜了。
走出小店时,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挤进店里的人收起雨伞,雨水顺着往下流,门口地板上积水一滩。
第二次来这,是和朋友们一起来的。我们点了不同的甜品,奶酪蛋糕非常惊艳,聊天喝咖啡,来来往往的人挤得小店水泄不通,不宜久留。我们点的东西不一样,结账时,都付了一样的钱,场面混乱,全场统一价。
那天和朋友从甜品店走出来的时候,看见马路终结处波澜壮阔的晚霞,心惊不止,
让我努力回忆起了第一次自己走出甜品店时,大雨夜里地面上晃动的光影。
在不同时间段里反射变动的光线,映照着伦敦百变的模样。
时间这样过去就很好。
Time Out London曾赞扬小店的甜品时,用了“Top-notch baked”来形容,
但却用大段笔墨吐槽小店的咖啡和服务,说在伦敦各种顶级的独立咖啡馆中,小店的咖啡简直不值一提。
关于服务质量,更用了“service can be chaotic”来形容。可是,那又怎样呢。
这络绎不绝的人潮,各种书籍杂志的高频力推,让古老的小店凌乱的世俗气,是越发丰饶热闹了。
每当提及“英式下午茶”或“法式甜点”,总会让人和“贵族”“奢华”和“传统”等词汇相关联。离寻常生活远了。
当你佯装熟络地走进一家久负盛名的皇室下午茶餐厅,心里边算计着最低消费,边努力回想着High tea 和Low tea的定义时,忽然想起了老爷爷的甜品店,那感觉真是既踏实又温暖。
小店地处灯红酒绿的SOHO区,却总是一副漫不经心的凌乱模样,
然而实惠好吃的甜点,又让食客们触摸到真实笃定的生活情愫。
话说,来小店随意选块蛋糕果腹的人,
有谁会在意它混乱的装修风格和并不怎么地道的咖啡拉花呢。
传说中所谓的神奇力量,就是这么一回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