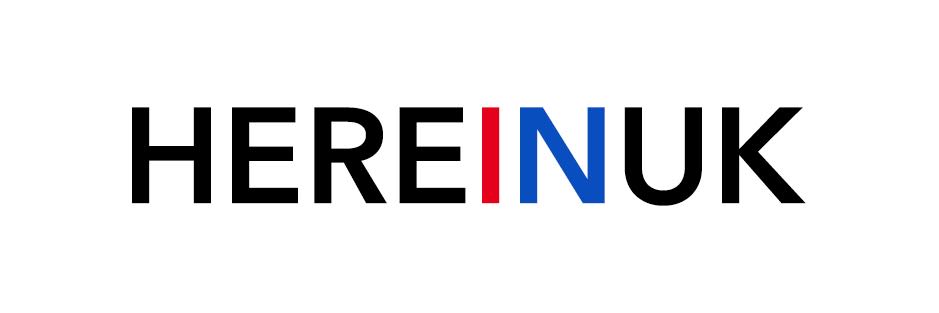英国小哥Chris Rory曾旅居日本,
回到家乡后,他在生活中依旧有着许多外国朋友。
因此,Chris对于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交流深有体会,
在他看来,非英语母语的人时常在无意之中创造出一些美丽且极具诗意的句子。
比如说,前几天他就和捷克室友发生了这样一段对话——
Chris:“我们的食物柜里有飞蛾(moth)。”

室友:“飞蛾是什么?”(室友不认识moth这个词)

Chris:“飞蛾就像可怕的蝴蝶一样,在橱柜里噗呲噗呲地飞来飞去(做出撒粉的动作)。”

室友:“哦,我知道了,那是橱柜里的鸟。(the cupboard birds)”

小哥顿时被这个诗意的形容迷住,连被飞蛾困扰的阴霾都一扫而空。

他发视频询问网友,在生活中是否也听说过类似的说法,
果然这并不是个例,很快,评论区就被外国人的妙语连珠淹没——
“我一个德国同事慌慌张张地找烤箱手套(oven gloves),因为想不起来这个词,同事便大喊说:‘那个能让人直接摸到热锅的东西(the hot pot touching able makers)在哪里?’”

“意大利人在找锅盖(saucepan lid)时脱口而出:他的帽子(hat)在哪里?”

“当有人忘了水族馆(aquarium)怎么说时,就会叫它液体动物园(liquid zoo)。”

“水族馆是‘鱼类博物馆’(fish museum)。”

“有一次我的法语老师忘记了‘公鸡’(rooster)这个词,她灵机一动,改叫它‘鸡的丈夫’(the husband of the chicken)。”

“德国朋友忘记了蛞蝓(slug)英语怎么讲,于是问说:‘没有家的蜗牛(snails without homes)叫什么?’
现在,每当我看到蛞蝓或者蜗牛时,我都会想到这句话。”

“我一个朋友说蜗牛是背着双肩包的蛞蝓。太可爱了。”

“我想不出葬礼(funeral)这个词,于是叫它‘死亡派对’(death party)。”

“在韩国,当我的学生想不起一个单词怎么说时,他们就会说一些与之相关的词汇,并加上‘朋友’两字。比如说,袜子(socks)就是鞋的朋友(shoe-friend)。”

“我的乌克兰继父最近和一个瑞士大叔交上了朋友,俩人都不知道大蒜(garlic)的英语叫什么,索性都叫它德古拉(Dracula)。”

“这些说法都太可爱啦。我的荷兰女友把日托所(day care)叫做婴儿拘留所(baby detention)!!”

“我一个意大利同事想说‘到了吃哈密瓜的季节’(melons were in season),结果说成了‘现在是专属哈密瓜的时刻(it is the moment of the melon)。’我太喜欢这个说法了,听上去好多了。”

“我的爱沙尼亚朋友忘了食谱(recipe)这个词,于是问我:‘你能把你的食物教程(food tutorial)发给我吗?’”

“没有橱柜里的鸟那么有趣,但有人把‘后天’(the day after next)称作‘明天的明天’(tomorrow’s tomorrow),听起来太可爱了。”

“我爷爷是塞尔维亚人,他不知道乌龟(turtle)怎么说,于是把它们叫做‘背着房子的青蛙’(the frog who carries his house on his back)。”

“交换的时候,我和土耳其还有日本女孩住在一起。我们都不知道沥水篮(colander)怎么说,所以干脆叫它‘面条烘干机’(pasta dryer)。”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把葡萄干(raisins)叫成陈年葡萄(Elderly grapes)。”

“如果忘记‘葡萄’怎么说,就叫它——长皱纹之前的葡萄干。”

“生活成本(the cost of living) = 活着的代价(the price of being alive)”

“和我一起工作的许多人(来自世界各地)都会用‘闪闪发光’(shiny)来形容外面天光明亮(bright outside)。每次想起来我都会微微一笑。”

“我的德国交换学生把手套(gloves)叫做手鞋(hand shoes)。”

“我曾在客户支持部门工作。有人会说‘从天堂释放我的数据’(Release my data from the heavens),意思是‘从云端删除数据(remove data from the cloud)。’”

“一个意大利男人本来想问我怕不怕痒(ticklish),结果却说成‘你受苦了吗?(do you suffer)’”

“我的挪威男友想不起菜花(cauliflower)怎么说,就叫它‘花椰椰’(flowie cowie),哈哈哈。”

“我认识一个人,把蛋黄(egg yolks)说成了‘鸡蛋李子’(egg plums)。”

“我叔叔不知道幼猫(kitten)怎么说,干脆就叫迷你猫(mini cat)。”

“很尴尬,有一次我把梨子(pear)叫成‘尖头苹果’(apple with a point),大家倒是立刻就明白了。”

“我朋友把墓地(cemetery)叫做‘死人睡觉的地方’(the place where dead people sleep),我再也不会干巴巴地说墓地这个词了。”

“我的土耳其老妈把流浪狗(street dogs)叫做‘自由狗’(freedom dogs)。”

“有一次,我记不起来‘电话亭’(phone box)怎么说,就说成了‘电话的房子’(phone’s house)。”

“我们小时候生活在法国,不知道怎么就长了虱子(lice)。我妈妈求医问药时,把它们翻译成了‘头发上的小访客’(little hair visitors)。”

“我在韩国教英语。教到身体部位时,我指着我的膝盖(knee),然后一个学生说:‘嗯,腿肘?(the elbow of the leg)’”

“我曾经和一个法国人聊天,对方一直把日落(sunset)描述为‘当太阳入睡时’(When the sun goes to sleep)。”

“我曾听到有人这样形容石榴(pomegranate):一张挂满了甜珠子的红脸蛋(a red cheek filled with sweet beads)。”

“有一次,我朋友记不得日语里‘灰尘’(dust)这个词,于是她叫它‘地板沙’(floor sand)。”

“一个希腊朋友想不起来马尾辫(ponytail)怎么说,于是叫它‘发泉’(hair fountain)。这个词现在我也在用。”

“我是法国人,当我想说坐立不安/手脚发麻(pins and needles)时,不小心说成了大腿上有虫子(insects in my legs)….”

“刚到英国时,我一直把电热水壶(kettle)叫成‘泡泡机’(bubble machine),因为我永远记不起来它怎么说。”

“我的德国男友将回形针(paper clips)称为‘办公室针’(office needles)。”

“我把战斗机(fighter jets)叫成‘杀手飞机’(killer planes),把我的爱尔兰朋友逗得哈哈大笑。”

“我和我的巴西老公坐在海滩上,一块海带(kelp)被冲了上来,他说:‘哇!水树!(a water tree)’”

“我在一家商店工作,有一次有客人要买浅色的面包,因为他们‘不喜欢黑暗’(don’t like the darkness),这种说法真是太有诗意了。”

“一个意大利出租车司机给我指路,他没有说‘顺时针走’(walk clockwise),而是说‘像钟表一样走’(walk as a clock)。我几乎每天都在想这句话。”

“我对我的寄宿妈妈说脚指(foot finger)而不是脚趾(toe),真不知道她怎么能绷住没笑出来。”

“我妈妈用‘花园蛇’(garden snake)来形容水管(hose)。”

“我记得我和一个德国人都忘了‘在平底锅上煎’(to fry on pan)怎么说,所以我们俩都发出了‘滋滋滋’的声音,然后开始无实物表演,比划自己手中拿了一个锅。”

看来,讲外语时不必担心出糗,
你眼中的低级错误,在旁人眼中,或许是诗一样美好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