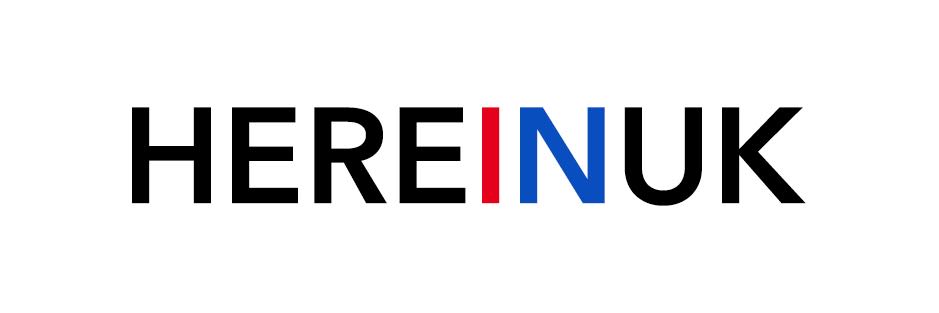多年来,范纳·约翰逊(Vanner Johnson)觉得自己的生活牢牢地行走在正轨上。
他住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家庭健康安稳。高中时,他和同学唐娜(Donna)相恋,两人从此形影不离,毕业后没几年便结了婚。
婚后,他们生下了两个儿子,一家四口过得很幸福,经常出门旅行、露营、钓鱼。
范纳对生活心满意足,不求更多,
直到某天,他发现自己不是小儿子的亲生父亲。而且,唐娜没有出轨。

(范纳和小儿子蒂姆)
这起家庭闹剧,要从2019年的夏天说起。
那时,唐娜看到基因检测公司23andMe在网上打折,检测套餐全场半价。他们给的报告可以展示用户的遗传状况,分析潜在的健康问题,还能绘制家谱。
唐娜觉得很划算,给一家四口买了套餐。
在盐湖城北部家中的厨房里,全家人嘻嘻哈哈地往小塑料管里吐口水,全当是一次有趣的家庭活动。

(23andMe的基因分析报告)
大儿子小范纳(Vanner Jr)和小儿子蒂姆(Tim)非常配合,吐好后,他们寄出了唾沫样本。
在唐娜和范纳结婚16周年那天,报告结果出来了。
范纳有点紧张,他暗想家里人是不是都健康。但在他的电子邮箱里,报告揭示出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范纳的基因和很多人相连,但这些人没有蒂姆。
换句话说,父子俩没有血缘关系。

(范纳一家,抱着狗的是蒂姆)
“我的第一反应是,有趣,肯定是检测公司搞错了。” 范纳告诉《卫报》,“我努力合理化整件事,比如,蒂姆是未成年人,所以他的结果不会立刻显示在网上。”
晚上回到家,唐娜的结果也出来了。
蒂姆和小范纳都显示为她的亲生孩子,但两人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其中小范纳的生父为范纳,而蒂姆的生父为“未知”。
“我当时想尖叫。” 范纳说,“什么叫他的父亲是‘未知’?我就是他的父亲!从他出生起,我就是他的父亲!”

(小婴儿,网络图片)
他看向妻子困惑又尴尬的脸,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很多人在这种时候,第一反应是怀疑妻子,但范纳没有。
多年来,他和唐娜日日黏在一起,很少分开。他们都有工作,妻子在儿子的学校当老师,不可能出轨。
假日里,全家人天天驾车旅行,彼此陪伴,唐娜不可能找其他人。
那只有一个可能性了:
当年生蒂姆时,做的体外受精出错了,把其他男人的精子放到唐娜的卵子里。

(单个精子被注射进卵子,想象图)
范纳和唐娜生完大儿子后,还想再要四个孩子。他们努力了18个月,总是失败,于是跑到犹他大学生殖医学中心治疗。
不孕的问题出在范纳身上。他做过疝气手术,伤疤把输精管堵死了,只能靠人工取精授孕。
医生给范纳做了睾丸活检,取出他的精子注射进唐娜的卵子里,然后再把受精卵放入唐娜体内。

(体外受精技术)
第一次体外受精,他们失败了;第二次,因为唐娜出现卵巢过度刺激综合症,卵巢肿胀厉害,医生将受精卵冷冻三个月,等她恢复健康后再植入。
整个过程很痛苦,但夫妻俩对结果是满意的。
“蒂姆是个非常可爱的孩子。” 唐娜说,“他有一头茂密的黑发,大大的眼睛,很漂亮。虽然他患有胃食管反流症,脾气也比较暴躁。”
“在蒂姆还是个小婴儿的时候,他就容易因为球而分心,但他的哥哥能安静地坐在我们腿上,一连读好几个小时的书。以前我就在想,那孩子的运动基因是哪来的,怎么和我们那么不像。”
“我以为这只是正常的兄弟姐妹间的个体差异。”

(女性怀孕,网络图片)
英国2021年到2022年的数据显示,每年有9万人做体外受精,手术出事故的概率只有不到1%,而且都是轻微事故。
美国的数据显示,每年诞生的400万新生儿中,有1%到2%是通过体外受精出生的。他们出错的概率和英国差不多,也非常低。
就和医院抱错孩子一样,输错精子属于极罕见事件,
但一旦发生,情况就变得非常灾难。
2016年,荷兰一家诊所发现,至少有26名女性不小心被注入了陌生男性的精子,其中一半人已经把孩子生了出来。

(体外受精)
诊所说,这是因为医护人员在注射精子的时候,使用了不符合规范的移液器。
每次注射完后,医生会更换移液器,但上面的橡胶盖不换。合格的橡胶盖应该装有过滤器,可那个没有,导致精子粘上去了。
这些荷兰女子把孩子留了下来,至少满足了当妈妈的愿望,但有些人却失去了监护权。
2018年,一对住在纽约的韩裔夫妇,花了10万美元做体外受精。
经过几个月的流程,医生终于把两个受精卵放到韩裔女子体内,承诺会给她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儿。

(双胞胎宝宝,网络图片)
但三个月后,医院检查出来说不是女孩,而是男孩。
夫妻俩很困惑,可到底是自己的孩子,性别没那么重要。等女子把孩子们生下来后,所有人都懵了……
两个男孩都不是亚裔,和他们长得完全不像!
其中一个孩子是亚美尼亚夫妻的,另一个没说种族,可能是白人,也可能是黑人。

(被搞错受精卵的亚美尼亚夫妇)
调查结果显示,是诊所弄混了受精卵。他们把一对夫妻的受精卵放入亚美尼亚女子体内,然后把她和丈夫的受精卵放到韩裔夫妇体内。
亚美尼亚女子受孕失败,没生下孩子,但韩裔女子成功了。
韩裔夫妇想保留孩子的监护权,毕竟是他们千辛万苦生下的,孩子还是个早产儿。
但法律并不允许,最后法院让亚美尼亚夫妇把孩子抱走了。

(生育失败,但没有完全失败……)
这件事也导致生错孩子的人不敢说出去。
2022年,以色列夫妻发现自己被放入了错误的受精卵,不敢公开说这件事。
他们花了数年时间才怀孕成功,女儿降生那一刻非常欣喜。发现医院搞错后,他们发誓不会让任何人把孩子带走,尽管他们的监护权在法庭上有争议。

(以色列夫妇发誓不会让孩子被抢走)
范纳和唐娜怕的也是这点。他们没有联系当初做体外受精的诊所,害怕对方把事情说出去。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确定我在法律上算蒂姆的什么人。” 范纳说,“我不知道他的亲生父亲会不会抢监护权。”
律师告诉他们,因为唐娜是蒂姆的生母,而她又是范纳的妻子,所以不用太过担心。
“根据法律,他还是属于我们的孩子,给我们一些安慰。但在美国,人们可以以任何事情起诉任何人。我们还是很担心蒂姆的生父。”
范纳犹豫了一年,觉得还是得把真相告诉小儿子。
他觉得这样的秘密无法在科技时代保留,蒂姆总有一天会知道,主动或被动。

(范纳和幼年的蒂姆)
“那是2020年10月,我带着蒂姆去吃冰淇淋。我想让一切尽量显得轻松点,就打算在车上说。” 范纳回忆道。
“我说,‘好吧,我们发现,当年做试管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不想用‘错误’这个词。”
“ ‘总之,不知怎的,事情弄混了,结果发现我不是你的亲生父亲。’ ” 范纳回忆到这里的时候,仍然流泪了。

(蒂姆出生那天的合影)
12岁的蒂姆情绪稳定,他说“没关系,你仍然是我爸爸”,然后低头继续玩手机。
范纳很高兴儿子早熟。
他觉得可以给孩子选择的权利,问他是否想知道亲生父亲是谁。
蒂姆点点头,于是他们又做了一次DNA检测。
这次,他们用了位于犹他州的Ancestry基因数据库,找到蒂姆的姑妈,接着找到姑妈的父亲(也就是蒂姆的亲爷爷)的讣告。
那份讣告列出老人所有孩子的名字,范纳挨个搜索,找到其中一个叫德文·麦克尼尔(Devin McNeil)的人。

(德文·麦克尼尔)
他和妻子建了一个博客,多年未更新,上面写着两人如何与不孕症斗争,如何尝试收养,又如何通过体外受精生下一个孩子。
那个孩子叫塔隆,他和蒂姆同龄。
唐娜深吸一口气:“看到这里,我们不约而同地‘哇’出声。”
看到德文,唐娜抑制不住有厌恶感,范纳的情绪也很微妙,他觉得德文比他高比他帅,有种挫败感。

(德文一家)
但两人觉得,既然德文有自己的家庭,便不用担心他会抢监护权。他有权知道自己还有个孩子,于是范纳通过电话,联系上他。
德文没有接陌生电话,他以为对方是推销员,但一连几天,见对方如此执着地打来,无奈地还是接了。
来电者有些艰难地说:“你不认识我,我叫范纳·约翰逊。我认为你和我们家有关系。你和你妻子有没有做过体外受精?”
“做过啊。” 德文困惑地回答。
“是在……犹他大学的医院吗?”
“是的啊,你怎么知道?”
“你很可能是我儿子的亲生父亲。”

(范纳一家和德文一家在聚餐)
挂了电话后,德文和妻子凯利商量,他们觉得对方可能是骗子。但他们收到范纳发来的蒂姆家谱图,上面有很多德文亲戚的名字。
唐娜和凯利交换了医院的治疗记录,发现她和唐娜在同家医院的同个时间段做体外受精手术。
医院给每对夫妻发了就诊号码,两家人的号码刚好是连续的。
最后,德文、凯利和泰隆都做了DNA检测,泰隆是他们俩的亲儿子,而蒂姆也是德文的儿子。

(两家人出去郊游)
显然,当年的体外受精手术出了很低级的错误,要么是仪器没有擦干净,要么是单纯输错了。
两家人都对犹太大学生殖医疗中心非常恼怒,中心不痛不痒地发布道歉声明,最后给了他们一笔赔偿金,达成庭外和解。
范纳开始担心,自己的精子去哪里了,会不会进入别的陌生人体内?
德文也有点害怕,他提供了不少精子,也许外面还有他的孩子。
“现在别人问我有几个孩子,我会说有三个半。” 德文开玩笑,“不希望更多了,以后不要出现这样的电话了。”

(范纳一家)
两家人计划与美国立法者见面,要求他们对美国生育行业进行更好的监管,加大对滥用精子、卵子和受精卵的惩罚力度。
“这几年我们研究下来,发现这块行业简直是狂野西部。” 唐娜说,“当大家走进医院的时候,是选择信任医生的,结果给我们搞出这种事。”
不过,此事也带来了好处,关心蒂姆的人变多了。
两家人在犹他州的公园见面,孩子们踢球、荡秋千,大人小孩一起坐在草地上吃午餐。

(蒂姆和兄弟姐妹们在一起)
蒂姆对自己的“新爸爸”挺感兴趣,两人都爱运动,行动举止非常相似。德文也把他当亲儿子,“只要他愿意,我可以一辈子在他的生命中出现”。
“现在我有两个爸爸了,还多了三个兄弟姐妹。”
小男孩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