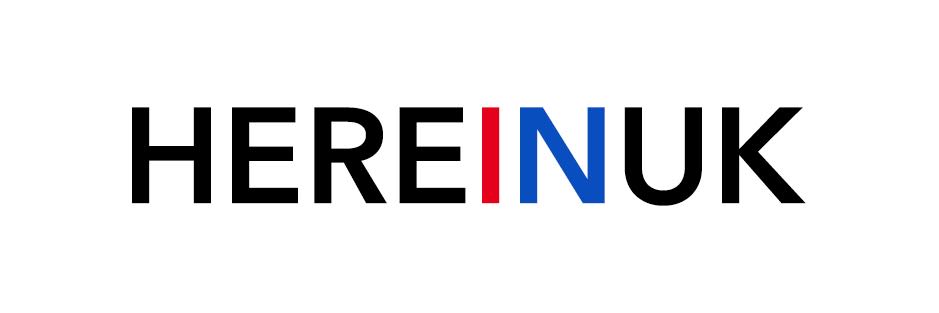提到对英国人的刻板印象,似乎总是离不开那几个梗:美食荒漠、男人秃头、超爱核查,以及“正儿八经老伦敦腔”:

(调侃英国口音的meme)
大家对英国口音的调侃并非空穴来风,实际上只要学过几年英语,应该就能很轻松地分辨英美口音,
而这两种口音因为各种影视剧的存在,还算是最好懂的,更难的还有各种非洲前殖民地口音、印度口音、苏格兰口音……
发展到今天,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听着不同地区、不同口音的人说话,往往在不知不觉间就已经将其他人的用词习惯学去。
这无疑意味着我们的口音正在发生杂糅——能让我们感到稀奇的“野生新口音”,已经越来越难捕捉了。
但其实,我们也可以“人工培育”新口音……
一群生活在南极洲的科学家,就无意间完成了这事。
–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南极洲并无常住人口,只有少数几个研究基地散布于这1400万平方公里的冰天雪地中,英国的罗瑟拉研究站就是其中之一。

(南极罗瑟拉研究站)
2018年3月,欧内斯特·沙克尔顿号带着26名研究人员抵达罗瑟拉研究站,随后在疾风骤雨中转身离开码头,26人对着船挥挥手,个别还兴奋得团起一捧雪,朝天上砸过去。
殊不知新鲜劲儿很快就会过,取而代之的是无穷无尽的黑暗、冰雪与孤寂——冬天要来了,再想看到白色以外的东西,得枯等六个月。
研究人员马龙·克拉克(Marlon Clark)总结道:“在这儿出了医疗问题想转移,比送人上国际空间站还要慢。”
“你彻底与世隔绝了。关于‘南极洲的冬天’有很多神秘的传说,你最强烈的感觉有两个,一是期待;二是意识到,‘OK,原来是真的,我得在这困很长,很长时间了’。”

(马龙·克拉克)
在接下来半年,这26位研究员面临着无休无止的黑夜与恶劣天气,拥有的却只有彼此。
克拉克与同伴们一起吃饭、工作和社交,与外界几乎没有任何联系,虽然有卫星电话,但费用太高,极少动用。
毕竟是去科考的,不可能带太多娱乐用品,于是最廉价易得的消遣就只剩聊天,天南海北,什么都聊,仿佛要把这辈子的话都聊干净。
在千万次对南极妖风的吐槽中,没有人留意到:他们的口音已经悄然发生改变。
–
除了日常的科考任务之外,克拉克等人其实还参与了一场大型社会实验,他们每隔几周,就要对着麦克风重复念电脑屏幕上的29个单词:
Food、Coffee、Hid、Airflow……录满十分钟为止。
这些都是日常用词,特别之处在于,它们的念法在不同口音之间有所区别。
毫无疑问,这是用来追踪他们的口音变化的。只不过当时他们还不清楚,还以为每隔几周就要完成这么一个怪异的任务……

(示意图)
半年后,26位研究员重返家乡,而录音被送到了德国慕尼黑大学的语音学研究小组进行分析。
结果令人振奋:一些单词的发音发生了细微的变化,这是出现新口音的迹象——一种独属于他们26个人的,全新的口音。
这26人有美国人、冰岛人、德国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口音五花八门,最终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
克拉克有些后知后觉地表示:“那边的一个朋友母语是威尔士语,英语口音特别重,但到撤离南极时,他的口音变得更像利物浦口音了(Scouse)。”
遗憾的是这位威尔士人并没有参加录音项目,不过有另一位德国女士参与了,经过半年的练习,她基本褪去了口音里的“德语味儿”,更像母语者了。

(研究站外的景象)
最好玩的要数他们发明的各种“南极词”。
克拉克举了几个例子,如果天气好,你就可以说“Dingle Day”;如果你要出去捡垃圾,就可以说“Fod Plod”。
“Dingle”在英语里是一个相当书面的词,意思是“树木繁茂的山谷”,跟天气一点关系没有……
至于“Fod Plod”,听起来甚至不像有什么实际意义,好像就是单纯地顺嘴,类似于我们说“叽里呱啦”……
能找到的最接近“捡垃圾”这个意思的,是航空领域的一个说法,指机场工作人员一步步在跑道上巡视,检查异物:

(关于“Fod Plod”的报道)
不用说也知道,这肯定不是日常生活会用的词,但它的的确确就是成了他们的日常用语,时间一长,没人觉得有什么奇怪了。
除了这两个以外,还有“Gash”,原意是“割伤”,但在南极却指的是洗涤、清洁、废物处理等工作。
“Smoko”,看着跟抽烟有关,指的却是茶歇/咖啡时间;
“Fid”,指被英国南极调查局“发配南下”;
“Doo”,指雪地摩托或雪地自行车;
“Firkle”,整理些东西,或者乱开玩笑;
“Gonk”,睡觉;
“Fox Hat”,本意狐狸帽,但在南极指的却是“基地的电影之夜”…….
感觉这已经接近于发明新词汇了。也许像这样再过上几百上千年,南极就会形成一种新语言……
–
慕尼黑大学的教授乔纳森·哈灵顿(Jonathan Harrington)总结道,南极实验就像是人类历史上发生了无数次的事的一个缩影,一群人与其他人群隔绝,最终导致他们发展出了新的方言、口音,乃至于语言……
“我们想尽可能地复制‘五月花号’前往美国时发生的情况。六个月虽然不长,我们只看到了非常非常小的变化,但的确,他们某些元音的念法已经有了变化。”

(五月花号,示意图)
“比如‘flow’和‘sew’当中的‘ou’音,更偏向声道前部了。另外他们发其他元音时,也在彼此靠拢。”
“因为当我们互相交谈,我们会记住对方的发音,这会对我们自己的发音产生影响。”
“实际上,每次与他人交流时,我们的发音都会互相传播与感染。随着时间推移,发音就会趋向一致。”
感觉也挺有道理?毕竟我们也有类似的例子:宿舍有一个东北室友,四年后,全宿舍人的东北话都说得无比正宗…….
如果是在与世隔绝的地方,也许是某个山谷,大洋彼岸的一片草原……每个人的口癖都会被放大和学习,时间一长,也就形成了全新的口音。
南极实验以小见大,大概在车马都不便利的年代,人类先祖们就是这样一代代创造了全新的语言,想想还真是挺神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