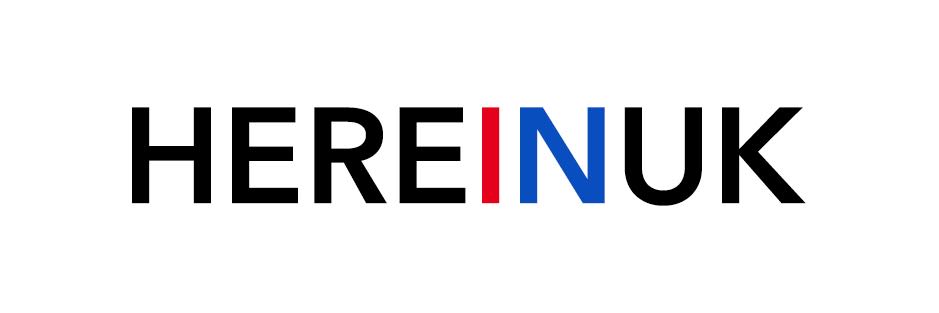简单来说,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指在绑架事件中,人质对绑架者产生情感认同,形成比较融洽的关系。
这种现象第一次被提出,是在197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发生的一起抢劫绑架案当中。
1973年8月23日,假释犯简·埃里克·奥尔森(Jan-Erik Olsson)和一名曾经的狱友克拉克·奥洛夫森(Clark Olofsson),试图抢劫斯德哥尔摩最大的银行。
他们劫持了银行的4名员工(3女1男),将人质关押在银行的一个金库中。
他们跟警方僵持了6天,8月28日,警方向金库投放了催泪瓦斯,这场抢劫绑架案以绑匪的失败而告终。
人质都获救了,但他们之后的反应,让人有些意外。
(被绑架的4名银行员工)
因为4名人质中,没有一个站出来指控绑匪,甚至还开始筹集资金为绑匪辩护。
他们都表示不恨绑匪,而是同情他们,因为绑匪没有伤害他们,而是一直在照顾他们,这让他们很感激。
人质中有一名叫克里斯汀·恩马克(Kristin Enmark)的23岁女子,她的表现更明显。
她说,她更害怕警察,警方的态度对她造成的生命威胁,貌似比绑匪更大、更直接。
她指责警方在这次案件中行动不力,根本不关心人质的死活,让人质不得不自己跟绑匪谈判,以保住性命。
在这个过程中,人质们觉得绑匪比警方的谈判人员更理智,警方谈判人员表现出的攻击性和煽动绑匪的行为,会危及人质的安全,这让人质对警方产生了深深的不信任感。
(人质克里斯汀获救)
克里斯汀还对当时的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开炮”。
在被绑架期间,她曾给首相打电话,向他吐槽警方的行动,
“我非常失望。我觉得你们是拿我们的生命当赌注。”
“我完全信任劫匪,也并不绝望,他们没有对我们做任何不好的事。”
“但是,奥洛夫,你知道,我怕的是警察会袭击我们,让我们丢掉性命。”
在42分钟的通话中,克里斯汀要求首相同意让绑匪和人质一起离开银行,双方发生了激烈冲突。
“你是这个国家拥有最高权力的人,你可以救我一命。”
“是的。”
“但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让绑匪跑到外面……他们迟早得明白,这种情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首相告诉克里斯汀,她应该宁愿死在工作岗位上,也不应该让首相屈服,满足绑匪的要求。
有报道说,克里斯汀曾对绑匪克拉克产生感情。
她也确实在回忆中说过:“我们很高兴他在那,因为情况变得不一样了。”
“他安慰我,握住我的手,他说‘我不会让奥尔森伤害你的’。”
但克里斯汀也表示,她对绑架者“没有爱或身体方面的吸引力”,她只是想活下去。
(人质被关押在金库里)
不光人质是这种态度,绑匪奥尔森也交代了类似的情况。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一开始他要杀掉人质,那会很容易;但随着时间推移,他跟人质之间产生了情感联系,下手就变得越来越难了。
(绑匪奥尔森被捕)
克里斯汀等4名人质的表现,让外界很不解,直到有人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
他是这起抢劫绑架案中警方谈判团队中的一员、瑞典犯罪学家和精神病学专家尼尔斯·贝杰罗特(Nils Bejerot),事后警方让他帮忙分析人质的心理。
贝杰罗特提出,人质是被绑匪洗脑了,跟绑匪产生情感纽带,反而害怕警察。
他将这种情况命名为Norrmalmstorgssyndromet综合症(Norrmalmstorg是案发地所在广场的名字),在瑞典之外的国家则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
(精神病学贝杰罗特)
随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心理学术语就通过媒体等渠道传开了,被人们熟知。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种心理疾病其实一直存在争议,一些学者对“究竟有没有这种病”都有疑问,甚至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根本就是杜撰出来的。
2008年,瑞典精神病学家克里斯托弗·拉姆(Christoffer Rahm)在论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精神病诊断还是都市传说?》中表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是精神病学诊断”。
拉姆认为,人质的行为是一种“帮助受害者应对创伤的防御机制”,这种机制在家庭暴力或其他形式的虐待案例中,也经常会出现。
(警方跟绑匪对峙)
2013年,《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出版了第五版。
这本书由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出版,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经常被当做诊断精神疾病的指导手册。
不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并未被收录到这本书中。
很多学者认为,这种现象属于创伤性联结(指受虐者对施虐者的依恋)或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学者们对此研究不多,也无法在对其的解释上达成共识。
(绑匪奥尔森被捕)
以上情况是在学术范畴内的,但之后几年,有人从其他的角度,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提出了质疑。
2015年,加拿大心理治疗师艾伦·韦德博士(Dr. Allan Wade)在一次演讲中表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子虚乌有,只是一个“都市传说”。
他曾采访过人质克里斯汀,听她详细讲述过那段经历。
“她是一位勇敢的年轻女性,她努力维护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她是心理学界最著名的女性之一,也是被误解最厉害的女性之一。”
他提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以及类似的概念,比如创伤性联结、受虐妇女综合症、习得性无助等,都是将焦点由实际事件,转移到受害者(尤其是女性受害者)的扭曲理论。
在韦德博士看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可以压制受害者公开谈论负面内容,是为诋毁女性暴力事件受害者而发明的概念。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让一位愤怒、疲惫又勇敢的年轻女性闭嘴,她只是从自己的角度讲述了事情的真相。”
“这跟克里斯汀·恩马克的心理状态无关,这是一种打压策略。”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示意图)
2019年,澳大利亚的调查记者杰西·希尔(Jess Hill)写了一本关于家庭暴力的书,名叫《看看你让我做了什么:权力、控制和家庭暴力》。
在书中,她把艾伦·韦德博士的理论更进一步,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称为“一种没有诊断标准的可疑疾病”,认为它“充满厌女情结,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
她还指出,2008年的一篇文献中说,
“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大多数诊断都是由媒体做出的,而不是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
记者在书中写道:“这种杜撰的建立,是一位明显跟案件存在利益关系的精神病学医生,为了抹黑女性暴力事件受害者而编造的谎言,他的第一反应是让质疑他的权威的女人闭嘴。”
“精神病学家贝杰罗特从未跟让他提出那种理论的那名女性(指人质克里斯汀)交谈过,从未问过她为什么更信任绑架她的人,而不是警方。”
(相关报道)
案件发生后的几十年里,人质克里斯汀也曾担心,是自己在那6天里做错了什么。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不再纠结了。
“理想的人质是一位守口如瓶、认为警方会保护她的女性。”
“当有人像我一样时,谁会说跟他们对立的话?你必须说他们是有病的、疯狂的,而不是看看警察做了什么。”
“是的,我害怕警察,这有啥可奇怪的?”
“人们害怕那些在公园里、屋顶上、角落里,身穿作战背心、戴着头盔、荷枪实弹、随时准备射击的人,这很奇怪吗?”
年过七旬的克里斯汀回想当初,仍然没有改变想法。
“当他们在报纸上写这些事时,我一点儿都不在乎。”
“我了解我的故事,我知道我的真相。”
“近50年后,我觉得自己没做错任何事。”
“我做了我必须做的事,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示意图)
无论是单纯的学术讨论,还是从其他方面进行解读,
关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争议,其实一直没有定论。
未来,恐怕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得出一个让大多数人信服的结论……